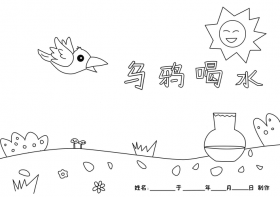杜鹃花依旧开放(1)
-
杜鹃花,依旧,开放,原文,标题,杜鹃花,依旧,

- 寓言故事-小马儿童故事网
- 2024-07-10 00:50
- 小马儿童故事网
杜鹃花依旧开放(1) ,对于想给儿童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杜鹃花依旧开放(1)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杜鹃花依旧开放(1)
发来拙作《杜鹃花依旧开放》,这是我悼念妻子的散文,自然与寓言无关。但文中有一个情节同寓言沾点关系。妻子去世第二天,在她装殓入棺之时,我把自己的寓言集放在她的胸前。她不识文字,一生无法阅读我的作品,根本不知道我在写些什么;这是我们一生最大的悲哀。我让她抱着我的寓言集,永远安息在故乡的青山上。
黄瑞云
二0一0年十一月十五日
一
我家住在一条山冲的最上头,一个单独的山村小屋,居屋对门是一条不大的山岭,翻过山岭有一道长长的山坳。那里有许多高大的松树,地面长满了各式各样的灌木,我们小时候常常在那里放羊,捡柴。一到春天,山里开满了鲜红的杜鹃花。杜鹃花,我们那些山里到处都有,但对门山的杜鹃花我印象特别深刻,就因为小时候常在那里活动。山坳那边又是一道山岭,那是由一系列大石头组成的石脊。石脊那边是一面长达五六百米的山坡,后来大多开垦成了山土。说不清什么原因,我们放羊或捡柴总不越过这道石脊,很少到那边山坡上去。山那边田野较为宽广,从我们的角度,那里被称为“外边”,而我们山里就称为“里头”了。山坡下面有几个小屋,叫做胡家湾。不知道什么时候,家里给我同胡家湾的一个女孩“订了亲”。女孩名叫胡玉莲,我从来没有见过,也不知道她住在哪个屋里。——许多年以后,玉莲告诉我,她到我们“里头”捡柴时看到过我,后来听说对了亲,她就不到我们这边来了。其实我家“里头”和她家“外边”相距不到三里路,却“老死不相往来”。
一九四八年正月十九,我正在家里铡牛草,父亲突然从外面回来,说胡家的祖母死了,女孩马上送过来。家里立即紧张起来,来了一些亲房,我二姐也回来了。快到中午的时候,外面响起了炮竹。我走出来一看,“新人”已经到了地坪里,头上蒙着一块布,竟然还是黑的,因为一时找不到红布,由两个女的搀着。我心里暗忖:“这就是我的妻子?”当她跄跄踉踉地被人搀着踏上我家堂屋前面石头砌的高低不平的台阶时,不知她心里想些什么,是否也有着某种人生的憧憬。
几天之后,我由一个堂哥领着,也以“新人”的身份上门了,送玉莲的祖母上山。玉莲的孝服上加了一块小小的红布,点出她的“新娘”身份。她不得不控制自己的悲痛,老是呆呆的。但到她祖母的棺材起动以后,她再也控制不住,呼天抢地,放声恸哭。天下着雨,她滚了一身的泥,头撞伤了,几个年长的妇女流着眼泪,把她死命地揪着。这样一直送上山,她仍伏在棺材上伤心地哭泣。
我们就这样成了所谓夫妻。
二
差不多四十年之后,我们到黄石生活在一起的时候,从玉莲偶然的闲谈中,我才了解到她童年时候的一些情况。
她母亲是平底人,在距我家二十多里的更深的山里,到那里去要翻山越岭。当她母亲来做“新娘”的时候,为了取个平顺吉祥,绕了三十多里较为平坦的路接来;坐了专供新娘用的彩轿。轿子走了三十里路,平平稳稳,到离家只有三里路了,经过小镇红溪坳,彩轿突然掉了底,众目睽睽之下,新娘从轿子底下掉了出来。这自然非常的不吉利,所以人还没有进门,丈夫就已经嫌厌她了。家里人常说是“千选万选,选个漏灯盏”。她母亲在这个家里没有过一天平顺的生活。她先生了一个儿子,智力倒还不错,不料长到十多岁得了重伤寒成为残废。之后连生了三个女儿。玉莲是她家最小的孩子,母亲怀她时得了水肿病,生下来没几天母亲就死了。她父亲当时想把这个没娘的婴儿送给别人,老祖母可怜这个小孙女,舍不得丢掉,情愿自己来抚养。从血盆里抱起的婴孩要抚养大谈何容易!那时候莫要说牛奶、奶粉之类无从看到,甚至没听说过,连买点饼干泡点浆水都办不到,祖母只能把红苕米饭在嘴里嚼烂一点一点地喂给孩子吃。婴儿本能地要吃奶,祖母把自己干瘪了的奶头让孩子含着。她父亲看了大发脾气,一手抓着她的小脚一甩,婴儿咬得太紧,来不及松开,以至把祖母的奶头咬出血来。婴儿甩到地上半晌才哭出声来。祖母抱起孩子,自己也伤心地哭起来。
这些童年往事,都是后来她祖母讲给她听的。当玉莲偶尔讲给我听的时候,我多次流下了眼泪,但她自己从不流泪,面带微笑,好像都很平常似的。
玉莲的父亲脾气暴躁,中年丧妻,儿子又是残废,家务负担沉重,心里非常之烦。“没有一天不发火,我们都很怕他。”玉莲说。但她谈到父亲的时候,还是满怀敬爱之情。可能她父亲后来比较喜欢这个小女儿。他抱她出去看过灯,略大一点常带她到小溪里捞鱼虾,到山上去捡蘑菇,甚至还带她去看过一次“人戏”。七岁的时候,祖母带她到姑姑家,对她姑姑说:“你看这造孽的孩子也能走这么远了,带大也好嘛,何必丢掉呢!”姑姑家在一个三面环山的小平地,田野中间有一条小河,可以在那儿玩水、抓小鱼、洗衣服;到姑姑家去,是玉莲小时候最高兴的事情。
一九四八年正月老祖母重病去世,玉莲被送到我家。突然之间,失去了慈爱的祖母,离开了自己的家,生活完全变了个样。当时我家种地主的田,劳动负担重,这是家里要娶媳妇比儿子大的原因。我比玉莲虽说只小两岁,但个子矮小,什么也不懂。我生长发育迟缓,二十岁后还长了四颗牙齿,身材才长高到一米七四。——说是成了夫妻,彼此也不说话,像陌生人似的。加以每天忙得晕头转向,除了吃饭很少待在屋里。
一九四九年秋天,家乡“解放”,那年秋征开始,父亲带领我参加了农村工作。父亲的能力比我强得多,做事很有气魄,敢作敢为。但我有点文化,能说会写,对上面的精神理解得快些。没有多久,我就取而代之,成为全区最年轻的干部,十七岁。解放初期,工作紧张,秋征,支援解放大西南,清匪反霸,双减退押,兴修水利,组织春耕生产;工作千头万绪,没日没夜。我白天很少在家,晚上即使回家也到半夜以后。工作可以说全力以赴,但成绩并不佳,自己感到很不适应。这些日子,我和玉莲很少在一起。岳丈家仅隔对门那个小山岭,一年也去不过两三回。她家没有女主人,只有一个残废哥哥,父亲差不多每天不在家。我们去了,玉莲就是主人,烧茶倒水,我倒成了客人,实在也很尴尬。
农村工作只有两年,中间还兼教小学,到一九五一年八月,我就读书去了。背个小小的大布背包,那是我母亲亲手缝制的,里面仅有一身替换衣服,一个日记本,别无他物,说走就走了。当时绝对没有想到,这一分手,我和玉莲会有如此长久的分隔,三十年!
三
我上学得到全家的支持,特别是我哥哥,他把整个家支撑起来。我已有家室,还有了孩子,都要家里人负担。因此家里只能在我离家时,给我一点必不可少的路费,除此再没有钱了。我全靠助学金,助学金只能解决学费和吃饭,长年累月,身上一个钱也没有。由于没有路费,所以并不是每年都回家。玉莲没有文化,无法书信联系,往往整年的不见面,也无任何音讯。她就这样默默无言地带着孩子,在家里顶班劳动。
我的学习成绩并不突出,总游移在十名前后。当然对一个没有系统读过小学和初中的学生来说,这样的成绩还算可以。一九五四年七月毕业于宁乡一中,随即考取武汉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成为我们乡和我的家族历史上第一名大学生。进入武大即当班长。由于没有一点经济来源,生活之苦可想而知。吃饭是靠助学金发的饭票,每个月靠卖掉几元钱饭票换点钱用于理发、寄信、买点纸张墨水什么的。在武大四年,进城不过几次,全是步行,没有搭过公共汽车,没有在城里吃过一餐饭。最后穷得连一条裤子也没有了,是向一个同学要了一条裤子离开武大的。生活虽然艰苦,但我受到老师的器重和同学的爱戴,又幻想毕业后会大有作为,总还是有一股力量支撑着,觉得前面还是花光百里,前程似锦。
绝没想到尚未毕业就一切都落了空。一九五七年一场反右,我们班受到惨重的打击。老班二十九个同学,竟划了十四个右派,十二名中右,全班只剩下“两个半”左派,创造了“全国第一”,我们班被称武汉大学“右派司令部”,震动武汉三镇,在全国也很有“名气”。我作为班长,可能受到某种保护,没有框上右派的帽子,只是“荣居”中右之首,被开除团籍。相当奇特的是一个受了严重处分的人,班长竟没有撤职,并一直当到毕业;但我从此成为有政治问题的人物。一九五八年毕业,要求回家度过学生阶段最后一个暑假,竟不被允许。毕业后分配到华中农学院,但是不能工作,只能下乡劳动。从此开始了长达二十多年的政治折腾。玉莲在乡里,不知道大学毕业是什么意思,更不知道我发生了什么事。按当时的政策,一般农村户口进不了城,何况我还是个内控右派分子,我们夫妻从此成为千里分隔的牛郎织女,似乎永远没有相会之期。
原文出处:http://www.chinafable.cn/content-6137.html
以上是关于杜鹃花依旧开放(1)的介绍,希望对想给儿童讲故事的朋友们有所帮助。
本文标题:杜鹃花依旧开放(1);本文链接:https://rc-yjbl.com/yuy/26848.html。
猜你喜欢
- 张老师-回首又见,记忆依旧 2024-07-19
- 关爱依旧 2024-07-19
- 艺术-青山依旧在 几度夕阳红 2024-07-19
- 杜鹃花依旧开放(2) 2024-07-10
- 杜鹃花依旧开放(3) 2024-07-10
- 杜鹃花依旧开放(4) 2024-07-10
- 杜鹃-杜鹃花 2023-05-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