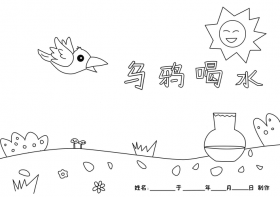杜鹃花依旧开放(3)
-
杜鹃花,依旧,开放,原文,标题,杜鹃花,依旧,

- 寓言故事-小马儿童故事网
- 2024-07-10 00:30
- 小马儿童故事网
杜鹃花依旧开放(3) ,对于想给儿童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杜鹃花依旧开放(3)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杜鹃花依旧开放(3)
七
从一九五八年武大毕业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二十年间,我先后有四年待在中学,四次下乡劳动合起来历时五年,文化大革命在牛棚关押多年;工作时负担很重,最难办的事往往交给我;一有运动总免不了批斗,而运动又总是接连不断,言必获罪,动辄得咎,迄无宁日。玉莲独自带着孩子们在乡下苦苦挣扎。在人民公社里奴隶式地劳动,收入却非常之低。生产队最好的年成一个劳动日十分工才三毛二分钱,而歉收年成一天只有一毛三分钱。但玉莲劳动一天只有六分工,因此好年成她劳动一天只有一毛九分钱,差年成一天才七分钱。一年所得永远买不回口粮。整个这二十年间,我的月工资锁定在五十三元上,没有一分钱额外收入。当时发表文章,出版著作,都要征得本单位组织同意,我的文章是不允许发表的,更不用说著作的出版了。我要维持一家三处的生活:年迈的母亲,妻子儿女和我自己。生活之难可想而知。玉莲从不诉苦,从无怨言,从没有提过一句关于钱的事。一九六四年冬天,我母亲在长沙诊病,我接她回去,钱到长沙就用掉了。过年的那天到达家里,身上只剩下九元钱。子由要去买盐没有钱,我掏了一元钱给他(因我还得留几元路费)。一年到头,好不容易盼望我回来,回来只给了一元钱。玉莲什么话也没说,仍然高高兴兴地过年。
那时玉莲正当盛年,在家里常常要受到一些无聊干部的骚扰。她又非常软弱,毫无抵抗能力,幸亏有我母亲的保护。母亲和玉莲隔个小院子住着。如有不速之客赖进门来,只要玉莲稍微示意,母亲就来救助。夏天一把蒲扇,冬天一个火笼,前来陪着媳妇坐到深夜,坐到天明。——玉莲终身感激母亲对她的保护。一九九一年新春,母亲以九十三岁的高龄去世,因玉莲晕车,我劝她不回去算了,但她坚决要回去,亲自送母亲上山。一千五百里路,一个晚上,三次转车,才到达家里。远远望见家门,她再没有力气了,匍匐在地,伤心地诉说:“我本来总想回来看你老人家,因为申六不在了,我没有脸来见你,现在却再也见不到你老人家了!”她的话很朴实,每一句都出自肺腑。
二十年间,在正常年道,我也只能回去十二天。我没有多少东西带回,连最粗劣的水果糖也买不了两斤,家里孩子多,每个孩子只能分几颗,自己的孩子也不例外。我差不多没有带过什么吃的给我母亲,别的人就更不用说了。为的是把那一点点现金交给她们。有一年我在旧货店买了一件短皮袄给玉莲,这是我给她买过的“最高级”的衣服;她非常高兴,总舍不得穿。
每年一回到家里,我立即参加劳动。犁田,挖土,割谷,堆草,打柴,什么农活都干。公社把田地分给农民自己种,玉莲就得当家做农活。虽说有我哥哥他们指导,毕竟要她自己当家,一个妇道人家,怎么也比不上人家男子汉,何况她还要带着孩子。我想尽量多做一点,多少给她减轻一些负担。每年暑假,收割之后立即要翻耕田地,要种冬季作物,要烧火土灰做肥料。烧火土灰要一定的技术,从前我只跟父亲哥哥烧过,没有当过家。后来每年回来我都烧,竟然堆堆成功。所有这些农活,都是同玉莲一起做的,她自然也很高兴。在我的回忆里,我们夫妻最愉快的时光,就是在一起劳动的时候。家里还有一项重要的活,就是担炭,要上三十多里外的乌云山才有炭担,翻山越岭,路也很不好走。开始我带子由去担。有一次我在一个山坡的岔路上走错了,走了一百多米才发现,但我不愿回头走,就从柴山中横过来。尽管不到二十米,但在几尺深的灌木中挑着担子很不好走,步步为难,走得满身大汗。突然看到前面山岩转角处,玉莲在那儿出现,肩上背担箢箕,手里提着饭缽,微笑着走了过来。我高兴极了,奋力从灌木丛中走了出来。她是来接我的。她突然出现的那个镜头,我永远也不忘记。我们也经常两个人去担,她担八十斤左右,我担一百二十斤。我比她走得快,往往先走到前头,再回头去接她一段。到乌云山去的路上,每一个山坳,每一个路口,都留下我们难忘的记忆。
二十年间,除了被关押的几年外,一般每年我都回家一次。由于经济上过于拮据,加以政治上的压抑,回到家里精神也是勉强支持,并不愉快。后来我女儿回忆那些年月,同别人说:“每到过年,我们盼望父亲回来,请人掐数,看哪一天到家。父亲回来了,家里就充满了欢悦的气氛。父亲本人却常常愁眉不展,笑容是强打出来的,当时我们不知道父亲受到如此之大的政治压力。住不了几天父亲又走了,总有好几天家里感到非常空虚。慢慢的我们觉得父亲一定有某种难处,以致我后来形成了一种反应,只要看到父亲神情严肃,心里就感到紧张。”
八
不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我竟然阴错阳差,进入了华中师范学院。华师对我倒也并不特别歧视,我得到了工作的权利,“复课闹革命”我又最先登上了教授中国古典文学的讲台。“四人帮”粉碎后,政策逐步宽松,我在华师也可以说站住了脚。我想到和妻子千里睽离已整整三十年,我们不应该再分隔。特别是女儿已经十五岁了,再过一年就带不出来了。但华师人事部门不肯提供帮助,我赴愬无门,一点办法也没有。我为此上书中共中央办公厅,上书国务院教育部党组,以我自己为例,为天下和我命运相同的人呼吁:国家对我们这类知识分子应该有个政策,经过多少年可以带家属,或者允许调回家乡也是一法,不应永远不予理会,永远不关心我们的命运。我们唯一的罪过,就是在农村娶了妻子,难道只有把这种苦命的妻儿丢掉才是唯一的解决办法。抛弃农村妻子的情况比比皆是,这与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不是完全相悖吗?汉宣帝不忘微时故剑,东汉大司空宋弘认定“糟糠之妻不下堂”。这些封建君主、朝廷大臣的品格成为千古美谈;难道我们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国家干部,就都要成为陈世美才合理吗?我措辞激烈,反正我豁出去了,而且我相信“四人帮”已经粉碎,邓小平胡耀邦当家的中国共产党不会再压抑我们了。
我的境况得到华师中文系师生的同情,甚至惊动了党委书记白瑞西同志。一九七八年我把九岁的小儿子申六带到华师上小学,一九七九年又把十五岁的女儿带来。一个人的口粮,两三个人吃,华师中文系的老师前前后后支援了我六百多斤粮票,白瑞西书记一次就送给我粮票六十斤。我在华师一附中教过书,附中四名女学生前来看我,临走时送给我一个小纸包。打开一看,里面是一叠粮票,其实总共只有十斤,是一两二两的票积起来的,那些粮票满是油腻,显然她们是从多少餐早点中省出来的,我点数时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中文系主任王相信,书记胡宜兰,古典文学教研室黄清泉、丁成泉、涂光雍等许多老师,都为我奔走呼吁。白瑞西书记三次同我谈话,希望我再坚持一下,不要轻易放弃华师。白瑞西原是中南民族学院书记,在华师缺乏基础,指挥不灵,即使他关照也没有办法。华师人事部门不肯支持,甚至对我进行愚弄。白书记最后一次同我谈话时遗憾地说:“如果我本人能掌握三至五个名额,我会给你解决,抱歉的是,我办不到。”
这个时候,黄石师范学院邵达成院长,中文系蔡伯铭主任——他们都是我的“五七战友”——向我伸出了援助之手,经过大半年的努力,得到黄石市有关部门的支持,蔡先生并亲赴湖南帮我疏通。如此我决计离开华师,投奔黄石。
一九七九年十月我把大儿子子由留在农村,接了玉莲和小孩子们先到武汉。一九八○年春节前两天,我叫十一岁的小儿子申六带队,“率领”玉莲和四岁的孙子金果先行到达黄石,带去一个条子给蔡先生,要学院第二天派车到华师接我,因为我有一些简陋的家具要运。大年除夕,车子来了,我和女儿站在敞蓬车上,迎着刺骨的寒风,告别我在这儿艰苦折腾了二十六年的武汉。坐在司机室里的司机的妻子可怜我衣衫单薄的女儿,脱下自己的风衣,披在我女儿的身上。车向东行,走上我人生的新的征程。
到了黄石,全家人在一间放破烂家具的屋里临时安身。这一天过年,我们什么也没有,临时上街买几个碗,几双筷子;临时买一点米,生个炉子做饭吃。厨房里放假关了门,邵院长三次登门,特别请了一位师傅给我们做了三个菜。这是我和玉莲结婚三十多年来开始真正的团聚,在外乡度过了第一个不无辛酸也不无欣慰的除夕。
九
到了黄石,是我一生能够正常地工作的开始,无论师院还是黄石市对我都很信任。进校两年之后我被评为副教授,其时我已是五十之年;第二年又担任副院长兼任学报主编,随后成为湖北省政协委员,黄石市作协主席,湖北省教委高职评委,社会活动陡然增多,工作极为繁重;但经济生活仍极为紧张。来黄石时,我的月工资六十四元,第二年加一级也才七十五元。在黄石我要维持一家六口(自家五口之外,还接了一个侄儿来上学)的生活,每个月要向远在家乡的八旬老母寄一点钱,老家一些亲属出了什么事故还得给予支援,而事故总是年年都有。邵院长非常关心,指示后勤部门让我妻子到厨房做临时工。第一天我送玉莲到厨房,她从农村来,笨手笨脚,言语不通,下午即被退了回来。第二天邵院长亲自送去,厨房才被迫接受。后来厨房看到玉莲这样老实,什么脏活重活她都去干,许多师傅对她都非常好。尽管增加了一点收入,我们仍很穷困,经常买不起菜,买不起煤。孩子们个个要上学,玉莲清早要上班,我更忙得不亦乐乎,每天都像打仗一样。买不起煤就烧柴火,八十年代前期有三、四年的时间,每个星期日我都带着孩子们上山打柴,主要是攀树上的枯枝,学校四周的山上我们都打遍了。家里的煤灶柴火灶都是我自己打的,没有请过人。每天天一亮赶忙到厨房里买一籔箕馒头,每人抓一个各奔四方。中午这顿饭由我来做,反正很简单。午饭后玉莲就把晚餐做好再去上班。几年生活就在这种困苦忙乱中度过。
无论怎么节省,经济还是敷支不来。这时候我得到了发表文章的机会。过往二十多年间,各种手稿我都有相当的积累,科研手稿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全部抄毁,但文学作品我设法保存了一部分,还有不少贮存在脑子里。每日白天对付工作,晚上备课之外就是写稿。写的有少数是论文,大部分是短小文学作品,特别是寓言。往往连夜写完,连夜謄正,连夜发出。草稿用针线一订,如果文章发表了,草稿就甩掉,没有发出又重新謄正再寄他处。每天晚上工作到凌晨两点多。到一切结束,疲倦之极,最后写几行日记的时候,连手上的钢笔都拿不住,常常掉了下来。更阑人静,天地阒然,听远方传来声声的鸡唱,这时候也未免感到辛劳和孤寂。一九八○年以后的几年间,我的小作品,主要是寓言,也有散文和诗歌,发遍全国,平均三天就发出一篇作品,是我一生发表作品的高潮。那时稿酬很低,一篇小作品几元钱,最少的一篇作品得过五毛钱。但总算是一点收入,帮我度过那些艰难的日子。工作自然十分辛苦,简直从来不休息,也无所谓假日和节日。幸亏我的身体不是铁打的,如果是铁打的早就磨融了。
一九八一年我四十九岁生日,而且碰巧是阴历阳历都在这一天,又刚好收到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我的第一本书;书很小,而且是游戏之作,但毕竟是第一本。上午我上完四堂课,回到家里,孩子们正等我吃饭。我对女儿说:“八,倒杯酒我喝吧!”八倒了一杯酒,轻手轻脚的送到我的手上。我端起酒杯,问道:“今天几号?”孩子们争着回答:“三月三日!”五岁的小果子也跟着说:“三月三日!”过了一会,我又问:“今天几号?”孩子们觉得奇怪,刚才不是问过了吗?女儿带着惊讶的眼神,微笑着说:“爸爸,你今天生日吧?”我也微笑着,作了一个手势,说:“再倒杯酒给我吧!”玉莲站在一旁,默无一言。下午,孩子们都上学了,我继续工作。玉莲打了两个荷包蛋,碗上搁了一双筷子,送到我的书桌上。我说:“怎么又吃?”她说:“我忘记了,今天是你生日。”我说:“那有什么,还不一样过。”
生活虽然紧张,但对玉莲来说,总算轻松了一点,即生活的重担不要她一个人来承担,而且主要由我来负责了。到了黄石好多年,过去那种担惊受怕的景况总还是萦绕在她的心头。差不多每天晚上都做梦,梦里故乡,仍然是过去的情景:连绵秋雨,红苕没有收回来,麦子没有下种;收成太差,怎么也比不上人家;孩子们没有吃的,没有衣服,如何度过寒冬。每天晚上,总是在惊恐中醒来,就向我转述梦中的情景,实在可怜,我为此写过一首小诗:“残年雨雪倍寒凉,儿女嗷嗷愁断肠。往日艰难萦梦寐,惊魂夜夜到家乡!”诗远不足以表达情意,但每一句写的都是真实的。
我从前不喝酒,来黄石以后才开始喝一点。买酒要花钱,经常拿起瓶子,没有酒了,我就说“算了,算了”。我们家乡农民都会做酒,玉莲如此也想自己来做。每次煮一斤米,拌上酒曲,发酵后成为米酒。她用一个破水瓢把底剜掉,做个小酒甑,中间插个小竹片作酒槽,放在锅上。米酒糟放在锅里。酒甑上放个装水的磁碗作为冷却器,然后生火蒸馏。每次蒸馏出一小瓶浑黄的酒。酒的质量并不好,但实在是用心良苦。酒糟她不会丢掉,放点辣椒用来作菜吃。八十年代前期买米要搭面粉,我们不大会作面食。面制品我只喜爱馒头,别的都不喜欢。于是她又学着作馒头。但技术总不高明,不是发不起来就是发酸了。我叫她莫作了,就吃面疙瘩也可以。凡是我喜欢的她都尽量办到,能力实在有限,往往很不理想,但她的心是尽到了的。
不必讳言,玉莲智力太低,又没有文化,对事物的认识能力很差,年纪很大了还像个小孩。有一天我上课回来,发现她在寻找什么东西,我问她找什么,她说找果子那块磁铁。几天之前她的一串钥匙掉进厕所粪坑里捞不上来,果子用一根线吊着磁铁一钓就钓上来了。我问她现在掉了什么,她说“我的肥皂滑进粪坑里去了”。她以为任何东西磁铁都可以钓上来。她在厨房里常常熏得眼泪直流,却总忘记把排气扇打开,烟都冒到厅里来了。给她说了,下次还是一样。当我不在时,她就把厅里的大风扇拉开。我不解何以不开排气扇却开大风扇。原来她认为风是风扇“生”出来的,大风扇肯定能“生”更多的风,更能把烟赶出去。这种笑话是经常要闹的。
有时玉莲也使我尴尬。我们平时吃饭,顶多两个菜,一个蔬菜,一个豆腐鸡蛋什么的,就算是好菜了。如果有点鱼肉之类的菜,她自己是从来不吃的,想都让给我。她也希望孩子们不要吃,常用眼神示意,叫他们不动。我给她说过多次,“菜不很多,孩子们也应该吃。我知道你关心我,但这样作,使我在孩子们面前都很为难。”她总是说:“小孩子吃什么,他们有吃在后!”无论怎么同她说,她都不听。有一回,我介绍武汉大学一位老师来师院工作。那位老师新来,我请他吃一餐饭,系主任和书记都住得很近,就请他们也来坐一坐。只有一斤多一点猪肉,再就是两个蔬菜。到吃饭的时候,我发现肉非常之少,而且多是肥的。特地请人家吃饭,如此贫薄,实在不好意思。到晚上我无意间打开碗柜一看,里面有一块瘦肉,约有三、四两重,原来她把实心的一块留下了,是留我吃的。我突然大怒,喝道:“你是怎么搞的!你真是!”她惊呆了,但一句也不解释。我心里一酸,立即改口说:“算了算了!”自己也不知道什么“算了”,感到好难过。这种使人啼笑皆非的事也经常有,但她保护我维护我的心是十分感人的。
我的寓言集终于出版,其他著作也逐渐得到问世的机会,工作多少有了一些成绩。为了不孤负父母和老师们的期望,我总想把过去耽误的时间追回一部分,夜以继日拼命地工作,没有多少时间和精力照顾家人,家务全压在玉莲的肩上,她仍和往日一样,从不诉苦,从无怨言。
生活就这样平淡而紧张地过着。但灾难总是紧紧地跟着我们,一场惨祸突然降临,一切平静和幸福的幻梦彻底破灭:一九八八年七月七日我们最有希望的小儿子申六在长江遇难!
原文出处:http://www.chinafable.cn/content-6139.html
以上是关于杜鹃花依旧开放(3)的介绍,希望对想给儿童讲故事的朋友们有所帮助。
本文标题:杜鹃花依旧开放(3);本文链接:https://rc-yjbl.com/yuy/26846.html。
猜你喜欢
- 张老师-回首又见,记忆依旧 2024-07-19
- 关爱依旧 2024-07-19
- 艺术-青山依旧在 几度夕阳红 2024-07-19
- 杜鹃花依旧开放(1) 2024-07-10
- 杜鹃花依旧开放(2) 2024-07-10
- 杜鹃花依旧开放(4) 2024-07-10
- 杜鹃-杜鹃花 2023-05-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