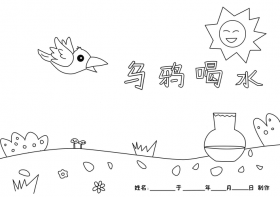杜鹃花依旧开放(2)
-
杜鹃花,依旧,开放,原文,标题,杜鹃花,依旧,

- 寓言故事-小马儿童故事网
- 2024-07-10 00:40
- 86
- 小马儿童故事网
杜鹃花依旧开放(2) ,对于想给儿童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杜鹃花依旧开放(2)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杜鹃花依旧开放(2)
四
反右之后不久就是大跃进,反右倾,建立人民公社,斗争一个接着一个。接着出现了可怕的“三年困难”,整个国家陷入空前的困境。
一九六0年的残冬,我回家探亲。家乡出现在我面前的是一幅多么凄凉的景象啊!原野萧条,庐舍空虚,饥饿夺走了许多人的生命。千山万岭的树木在大跃进中被全部砍光,到处童山濯濯。村落里一片荒凉,听不到任何鸡鸣狗吠的声音。人民公社的食堂已经实际解散,我自己的大家庭也自然解体,玉莲已完全“独立”生存。分给她的全部财产是一间破房子,自己原有的一张床和一个柜子,桌凳还在食堂里没有收回。靠墙平放着两个土砖用来生火做饭。所有铁制的饭锅菜锅全在一九五八年打碎用来“大炼钢铁”,亦即把有用的铁器炼成废铁;做饭烧水都用一种粘土烧制的煨子代替。女儿彬子在年前饿死了,一岁半的小女儿也奄奄一息。玉莲从前体态丰满,如今已是骨瘦如柴。我回来了,她抱着小女儿坐在门槛上流着眼泪,没有放声大哭,我们彼此默默相对。她极力控制着自己,免得引起我伤心。——许多年以后,谈起女儿死的惨状,她告诉我:这孩子太可爱也太可怜,所有来的邻居都哭了。她自己哭得死去活来,紧抱着小棺材不肯放手,邻居财三老汉想把她抱开,把衣服都撕破了。“要不是为了两个孩子我都不想活了”。——到家的第二天,我要儿子子由引我到彬子的坟上去。一个小小的土堆开始长草了。这里原是一座很大的松树林,全被砍光了,地面的灌木同样被芟除,树根也大多刨掉了。残存的杜鹃花树却伸出了尺把长的枝条,而且打了花苞,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春天,它们可不知道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变化。我采了许多杜鹃花枝子围着坟堆插了一圈,蹲在坟边哭泣。儿子脱下帽子,不断用手背擦掉眼泪。唐宪宗元和十四年韩愈罪贬潮州,随行小女途中病逝,草草安葬,后来他写了一首沉痛的诗云:“数条藤束木皮棺,草殡荒山白骨寒。致汝无辜由我罪,百年惭恨泪阑干!”而我愧为人父,连草殡荒山的责任也未能尽到,其惭恨更何如之!尔后数十年间,每读韩公此诗,未尝不潸然泪下。晚上玉莲对我说:邻居福嫚告诉她,“你到山里哭去了,她说做父亲的到底不同。算了,她什么也不知道了。以后你一个人在外面,不要再想她了。”
食堂虽已解散,口粮仍由生产队按日定量发给。玉莲每天的口粮是十六两制六两(相当十两制3.75两)。九岁的儿子每天四两(2.50两),两岁的小女儿二两(1.25两)。有时发的还是红苕米或者麦麸子,不全是大米。玉莲那一点点粮食还吃不到口,不得不匀一点给孩子吃。儿子每天提个大竹篮,到处寻找可吃的野草。每天晚餐全是吃草,里面仅放一点盐,油是绝对没有的。
小女儿一生下来就碰上大跃进,大人们日日夜夜,大炼钢铁,大开荒,大搞人海战术。所有的男男女女全都成了农奴,一律统一调配,今天驱到这里砍树,明天赶到那里开荒;小孩子当然是不能带的。小女儿同其他几个孩子,全都由我母亲照管。开始母亲还可以给他们喂点米汤或南瓜汤之类的东西,大饥荒一来什么东西也没有了,只能喂水,等待各自的母亲回来喂点什么。开始小孩子们挣扎着啼哭,到后来哭也不哭了,全都都变呆了。我想到小女儿一生下来就这么苦,给她取名叫黄连苦,但我母亲不同意,认为名字还是应该美一点。我想天知道她能不能活下去,干脆不要名字了,因为她行六,就叫六妹子。有一天早上,玉莲抱她起来,因为身体虚弱,全尿湿了,那是用一件大人的破衣服包着的,尿的透湿。玉莲给她换衣服,脱掉湿的,简单地抹一下,包上另一件破棉袄。我坐在旁边难过地看着。换完以后,孩子坐在玉莲的膝上,忽然用瘦瘦的小手在我的手上拍了一下,竟然露出了一丝笑意。大概她觉得身边这个人同她有点什么特殊的关系。我伸手把她接过来,抱在怀里,眼泪簌簌地滴在她的身上。她来到这世上一趟,这是仅有的一次对我表示了一点情感;在她心里,还未必有“父亲”这个概念。过年的那一天,子由到我二姐家里,我二姐给了他一小把豆子。他舍不得吃完,给妹妹留了十来颗。玉莲抱着拈给她吃,她不肯吃,并且做着手势。玉莲说:“这要死的,她还是要她那个木碗。”那是几个月前,子由从街上花一毛五分钱买的一个小木碗,是用一小段棕榈木作的,小巧玲珑,有一圈一圈自然的花纹。孩子很喜欢这个小礼物,吃东西都用它。玉莲从地炉子灰里检起小木碗,抹了一下,拿给她,几颗豆子放在里面,她一颗一颗地拈着吃。这种执拗的性格,同大女儿非常相似。——三个月之后,孩子终于饿死了,那个小木碗就放在她的小棺材里给她殉葬;这是她来到这个世界上拥有的唯一的财富!尔后几十年间,我每次回家,想看看两个孩子的坟墓,再也找不到了。那些山头经过反复多次的开荒,地面的一切都改变了;我们的可怜的孩子们重新化作了泥土,化作了飞灰,没有留下任何一点痕迹!
我的假期只有十来天,过了年就得重上征途。玉莲想给我一点吃的东西路上充饥,可家里找不出任何可吃的东西。我母亲的口粮同样少得可怜,是绝对匀不出来的。我家有几棵枇杷树,树皮早已剥光吃掉了。剥了皮的枇杷树立春后还会挣扎着开一次花,但不可能结果了,到夏天就全部枯死。玉莲把枇杷花摘了下来,还挖了一种什么草根一起捣烂,草根汁有粘性,将枇杷花捣碎和合,做成十一个小饼子,烘干,作为我路上的“点心”。从前在大家庭的时候,我出门玉莲是从来不送的。这一次一反往常,当我还和母亲告别的时候,她已挑起行李等着。“走,我送你!”她轻轻地说。她在前面走,我在后面跟着。她没有话说,只是默默地走。一直走上了李家崙,这是一个几十米高的山岭。到了山顶上,她把行李换给我,说一声,“你走吧!”我掏了一个枇杷花饼给她,她不肯要,推来推去,她把饼子掰成两半,还了一半塞在我的袋子里。分手了,她不说话,也不流泪,只是重复一句,“你走吧!”她站在那儿,一直望着我走下山去。走了很远很远,我回头一看,她还站在那儿。她没有挥手的习惯,只是呆呆地望着,身子略微偏一点,一动也不动,像一尊石像;一直到我完全看不见她了,也许还要站很久。——此后即成为常例,每年我回家,走的时候她都送行。我家去娄底有好几条路,因此送别的地点也不固定,每次送十里八里,最远的送过二十多里,总是在某个山口,某个桥头,默默地分手。这种黯然神伤的送别,持续了整整二十年。
到一九六0年,我们已是十多年的夫妻了,过往那些年月,都平平淡淡地过去;只有这时候,我们成了在死亡线上挣扎的伴侣,我们的心才贴得紧密,我们的命运的绳索才纠合在一起无法分开。尽管分别的时候没有话说,内心实在是难舍难分。到了娄底,上了火车,任车箱摇晃着疲倦的身子,听车轮匡当匡当地响着,把我送向远方,脑海里总晃着妻子孩子的身影,想到她们在挨饿,她们随时都可能夭折,心情通夜的不安。天亮的时候,向车外望望,只见连绵不断的青山飞速地向南方奔去,心里感到非常沉重。“征衣还带故乡尘,万里飘然一叶身。待晓凭台望窗外,青山犹自向南奔!”这是当时在车上诌成的一首小诗。
五
那年暑假,我又一次探家。情况一点没有好转,甚至更加严重。小女儿已在这年春末夏初夭折——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我们丧失了许多亲人。尤其是父亲的死给予我们全家惨重的打击。他一生当过四个东君的佃户,为我们兄弟姊妹的成长耗尽了精力,并寄与莫大的希望。他的死在我的心灵上造成极大的创伤。我的嫂子和一个侄女,还有弟媳,都或前或后死去了。嫂子饿死后没有棺木,,男人们也没有力气去挖掘坟墓,用一床破篾席将遗体一卷,放进一个土山上的红苕窖里,掩上黄土;她的一生就这么终结。由于三个姐姐尽全力维护,才保住了我母亲的生命。玉莲娘家的境况同样悲惨,她父亲也去世了,家里只剩下她的残废哥哥和哑巴嫂子。许多人得了水肿病,到处是一片凄凉。没有欢乐,没有笑容,甚至也没有眼泪,人们唯一的考虑是怎样活下去。
秋收在即,却看不到多少希望,粮食一直是定量供应的,仍然少得可怜。有少数人却依然心广体胖,饥荒对他们没有害处,人们心里明白是怎么回事,但是无可如何。稗子总是早于谷子成熟,公家田里的稗子又特别多。有一天,玉莲带着我冒着炎热到田里去捋稗子,捋回来立即炒干,稗子籽粒小,壳却很厚,炒时操作太急,全烧成了焦炭。把它连壳磨碎,粉末全是黑的。用水一和,烧开,仍当作稗子粥来吃,又苦又涩。哥哥从门口过,手里拿着一个饭碗那么大的小南瓜。他说:“你们这怎么吃,把这个南瓜给你们吧!”我们把南瓜切成小块,放在墨黑的稗子粥里一煑,南瓜块都变成黑糊糊的了。这样一个小南瓜已是非常难得了的,当时已无法种蔬菜,任何蔬菜长出来还是苗子,过路人就会就手掇起往嘴里送;就像饥饿的羊子,看到任何野草都抢着吃,不知我哥哥在哪个偏僻处竟然还种了南瓜。
假期结束,玉莲送给我路上吃的食品就是几个小小的稗子粑。她送我翻过了李家崙,仍然不肯回转,又过了斜塘,在邪塘出口的小桥上,我再不要她送了。当时我得了严重的肝炎,尽管我没有给家里人说,但看到我面黄肌瘦,疲沓不堪的样子,她心里是有数的。生命是如此地脆弱,随时都可能倒下,今朝一分手。不知道明年还能不能见到。一种生离死别的哀伤,沉重地压在我们的心头,但我们彼此都不说破。“屏营衢路侧,执手野踟蹰”,没有说一句话,默默地分手。我走了好远好远的路,回头看她仍旧站在那桥头上。
饥馑困苦的生活,不是一天两天,不是一月两月,而是将近三个年头,上千个白天黑夜。没有天灾,没有战乱,仅仅是一种疯狂意志的恶性发作,就使亿万生灵陷于绝境,并最终葬送了几千万人的生命!这是一个怎样的人间世!
到了一九六一年底,政府终于开恩,分给农民一小块自留地,而且允许开一定的荒地。玉莲如此也和其他农民一样上山开荒,种一小块地小麦。第二年打了几十斤麦子,“丰收”带给她无比的喜悦,也挽救了她的生命。——时间过去了四十年,一直到去年玉莲在病中说着呓语,还喃喃自语:“我们打了一箩麦子,孩子们有糌粑吃了!有糌粑吃了!”可以想见,饥荒在她的心底留下了多么深的疮伤!
我这方面由于发生了一件奇特的事,意外地救了我的命。当时我在华中农学院附属工农中学教书,和我同住一间房“非常友好”的同事广西人韦某偷看了我的日记,并且摘录向党委汇报,我被认为有严重思想问题,停止工作,发配到汉阳水洪口一个农场劳动——当时有内部朋友向我透露了消息,我一时都弄懵了,不知道情况到底如何。直到文化大革命我在教院受斗争时,到农院附中调查的人在会上揭发我的罪状,公开了据说是我日记中的话,谜底才彻底解开,无非是说我认为大跃进有些作法脱离实际,也记述了一些农民没有饭吃的事。即使经过这位“友好”人士篡改过了的话也没有什么大逆不道的内容。时至今日,大概没有人会认为我说的过分了,而在当时,一加上攻击“三面红旗”的罪名可是要命的事。——多承这位朋友的“关怀”,真的救了我的命,口粮由每月二十三斤(实际是不可能都吃到口的)加到四十五斤,农场里还可捡些当地农民秋收后残留的红苕高粱掺着吃。而劳动对我来说不仅不感到是一种惩罚,而且是一种乐趣。农场里凡属知识分子,绝对没有人可以和我相比,加以我和劳动群众一贯的融洽,这段生活我过得非常愉快。一年下来,我的体重增加到破记录的六十九公斤,身体完全恢复。一九六二年秋后评奖,我评得全农场唯一的甲等奖,奖励一百二十斤麦子,这在当时比得上一个金奖。我把小麦磨成面粉,还挑了一部分回去,那一年在家里度过了一个难得有的祥和的九月。
一九六三年我们得到了一个小女儿八八。她是夏天出生的,出生时只有我母亲来招呼一下。几天之后,玉莲就得下床干活,做繁重的家务。孩子没有奶吃,没有糖吃,没有一件新衣服,但玉莲爱若珍宝,尽心尽力把她养活了。比她大十三岁的哥哥不断给我来信,信都是电报式的:“妈妈生了一个弟弟。”“弟弟会笑了。”“弟弟生了两颗牙齿。”他写的都是弟弟,我以为是个男孩,冬天回家才知道是个女孩。半岁了,瘦瘦的,一点不认生,我抱起她就笑,真笑得像花一样,我相信世界上绝对没有这样美丽的花儿。那年冬天下大雪,我解开棉袄的前襟把孩子偎在怀里。这个寒假我们过得比较恬静。我们失去了两个女儿,上帝终于又恩赐我们一个女孩,给我们增添了极大的慰藉和欢乐。
那一年我进入了湖北教育学院。
六
大饥荒过去没有多久,阶级斗争的弦再次繃紧,批判斗争接连不断。一九六六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发生了!我立即被孤立,被称为漏网右派分子,很快就投进了牛棚,和家里完全断绝了联系。
一九六八年冬天,我被五花大绑,解回家乡。一个雨冻风寒的下午,我到达小碧公社,立即被送进了临时的监狱。那是一排楼房,有几个房间关的都是小学教师,大多都认识我;我走过的时候,他们都在窗口看着。其他房里关的是农民,大多是“外流犯”,我基本上都不认识。同我关在一起的叫黄小秋,出身贫农,是刚从江西抓回来的。这是一个非常和气的人,比我大十多岁。那些农民毫无顾忌,交错着前来看我(因为监管人员都是熟人,并不那么严厉)。他们说:“你是黄老师吧,我们早听说了,你什么工夫都会,一点不要怕,回来就回来吧!你家里从前还不是种田,回来也无非是种田。”他们的看望给了我很大的安慰和鼓励。十九年前这儿最年青的农会主席,本乡第一名大学生,于今成了罪犯,消息震动了整个公社,无数条关切的线把信息通到了我家里。傍晚时分,我侄儿子腾和儿子子由来到牢房。两个孩子拉着我的手,我感到他们的手瑟瑟地发抖。我很生气,大声地说:“你们干什么!出了什么了不起的事!”我知道,这个时候训斥他们一顿是对他们最好的安慰,让他们知道我并不害怕,没什么大事。但在昏暗的灯光下,我发现儿子的头发稀稀拉拉,肯定是害过一场大病掉了头发,心里不禁一阵悲怆,但我没有说什么。他们走后,黄小秋说:“你的被子这么破怎么盖,我们一起睡吧,你的被子垫着,盖我的被窝。”两个人和衣睡在楼板上,把小煤油灯也熄了。楼板上方不到两米就是屋顶,寒冬的雨点打在屋瓦上沙沙作响。在外地,听到雨声我往往想念家乡;今夜家乡的雨啊,你们的响声说不清给了我怎样的感受呀!快半夜了,忽然听到楼门外一个非常熟悉的声音:“怎么搞的,灯也没有一个!”是玉莲!我一翻身起来。黄小秋也连忙起身,划了一根火柴,把小煤油灯点亮。玉莲不善言辞,也从来不叫我的名字,她之所以大声地说话,等于通知我,她来了。听到这句简单的话,我比听到任何情意缠绵的话还要亲切。打开牢门,她进来了,给我送了饭来。她穿着青布上衣,下半身满是泥水。穿的浅口套鞋根本不管用,里面都进了水。天这么黑,泥泞路滑,亏她怎么走来的。她蹲了下来,解开布包,一大碗饭,缽子里甚至还燉了一只鸡。她神情坦然,什么话也不问,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就像从前我在外面劳动她送饭来一样。只摸了一下我的肩膀,问我冷不冷。我一边吃饭,一边轻轻地说:“告诉妈妈,没什么事,不必耽心。”她点点头,什么也不说。我吃了饭,她收拾碗筷。我说:“这么黑,你怕不怕?”她说,“不怕。”我知道她怕走夜路,何况还下着雨,于今也只好说“不怕”。我不能送她,让她一个人没入深深的黑夜,雨还在淅沥淅沥地下着。——二十多年之后,到了黄石,偶然谈起那天晚上的情景。她告诉我:那天傍晚,好几个好心人传来消息,说我被捉回来了。一家人围在母亲的房里,一片惊惶,感到大难临头。倒不是怕我真有什么问题,而是怕被武斗,在这之前打人打得厉害。母亲一直等到玉莲回来,非常着急,全家人都通夜没睡,不知道明天会有怎样的灾难,可那天晚上在我面前她一点没有流露出来。
以后每天玉莲都来送饭。这年四月,我们添了小男孩申六。玉莲说:“我想把孩子抱给你看看,但八八也要跟着来,两个孩子我带不动,明日姐姐回来我再带他们来。”姐姐回来了,玉莲抱着小的,姐姐牵着八八,来到牢房。八这年五岁,听说我到了公社,每天闹着要来。一进牢房,看到这么个情景她惊呆了。我抱抱她,她默不作声。申六还只有半岁多,自然什么也不懂。我们的大孩子都长得比较清秀,这孩子却很特别,宽大的前额,双眼睁得滚圆,一眨也不眨。黄小秋说他会看相,一看到申六就赞赏不迭,说这孩子一定非常聪明,将来大有出身。玉莲很为自己的孩子得意。
据说湖北教育学院解送我的人要求公社开大会对我进行斗争,公社没有同意,只在大队开了会。来了约莫一百多人,没有一个贫下中农揭发我任何问题,批斗我的唯一角色是教院去的造反头目吴某,在会上吐沫横飞,揭发我二十八条罪状,这些罪状差不多每一条都很离奇。——随便举两条吧:文革前,我所在的教研室里林文勉蔡伯铭和我参加了对一种语文教材的审查。教材节选了毛泽东的《愚公移山》,从“古代有一位老人,住在华北,叫北山愚公”选起。林文勉认为应加上前面“中国古代有个寓言,叫做愚公移山”那一句,因为毛主席明说是个寓言,不这样选,孩子们可能认为真是事实,会不会有副作用。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林文勉这些话就被无限上纲: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怎么会“有副作用”?说“有副作用”不是说他“有毒”吗?《愚公移山》是“老三篇”之一,说《愚公移山》有毒,也就是说“老三篇有毒”。当时林文勉蔡伯铭和我被打成“三家村”,凡是我们之中任何一个人的话都可以转嫁到其他两个人身上。吴某在斗争我时就径直说我“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说毛主席的老三篇有毒”!我曾写过一首读毛主席诗词的词,词中有“反帝反修大业,馀事到斯文”这样两句。后来被抄查出来,教院有名的丑八怪李某批斗我时,将词句深文周纳,说“毛主席诗词是伟大领袖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怎么说是‘馀事’?这不等于说毛主席吃了饭没事干!”吴某斗我时把丑八怪的话接过来,指着我说:“伟大领袖毛主席日理万机,黄瑞云竟然说毛主席吃了饭没事干!”二十八条罪状都是这样的杰作。斗争会开了一个多钟头,我又被重新押回公社。
第二天玉莲来送饭时,我在牢房门口刚好碰上吴某——吴某曾经和我共过事,原来关系并不错;但现在他是造反干将,我是牛鬼蛇神,他斗的也就特别凶狠残酷——我说:“老吴,你昨天揭发我那么多罪状,有哪一条是落实了的?”吴某说:“我是出发时拿的一份材料,照着讲的。”我说:“在学院你们怎么斗都可以,人们知道是怎么回事。你想过没有,这是我家乡?你可以斗个痛快,贫下中农将怎样理解?”吴某一时也很尴尬。从不插话的玉莲,突然说道:“一点关系没有,没有人会相信!”下午我弟弟来了,他说:“大家听了都好笑,这种胡言乱语我们听得多呢,就当他是狗叫!”原来他们都对这种“创作”高度的藐视。
这些人要把我赶下农村的目的没有达到,关了一个多月只好又把我解回武汉。离家的前一天,玉莲最后一次给我送饭,对我说:“明天我不来送你了,八八总要跟着来,申六我也抱不动;我叫子由来送你。”我得到监管人员黄松乔的允许,倒送她一段。我们慢慢地走着,一直走到了山冲的出口,夕阳下面,远远地望得见山岭上从我家到她家我们常常经过的那块大石头,彼此都无限地伤怀,无限地依恋。
这里应该提到黄松乔这位难忘的朋友。我在公社换过几次牢房,后期监管我的就是黄松乔。他是一位复员军人,比我略小几岁,对我很同情。偶尔有什么无聊的人试图侮辱我,他就毫不客气,把那些人赶走。按公社规定,他得同我住在一起,以便于监管。他拿了许多稻草垫在地板上,自己抱一床很大的印花被来,对我说:“你的被子太薄了,就盖我的,没有关系,我不会来睡。”人生在世,在遭难的时候,能得到这样一位朋友实在令人感激。后来我们建立了很深的友谊。去年玉莲去世,黄松乔还亲自来送她上山。
原文出处:http://www.chinafable.cn/content-6138.html
以上是关于杜鹃花依旧开放(2)的介绍,希望对想给儿童讲故事的朋友们有所帮助。
本文标题:杜鹃花依旧开放(2);本文链接:http://rc-yjbl.com/yuy/26847.html。
猜你喜欢
- 杜鹃花依旧开放(1) 2024-07-10
- 杜鹃花依旧开放(3) 2024-07-10
- 杜鹃花依旧开放(4) 2024-07-10
- 杜鹃-杜鹃花 2023-05-03